-
拼50歲提早退休,人生卻「暴跌」不掉速度陷阱,學「CASH」法穩定增值
-
「抗癌湯」真能逆轉癌症?猛喝恐住院!別一味跟著蕭萬長喝,防癌營養要這6種
-
每月「盲存」退休金事倍功半!掌握「所得替代率」月領5.8萬攻略揭曉
人生轉眼一瞬,為親人送別時,更能明白這道理。人身難得,要好好活;人生如戲,你玩得夠盡興嗎?為什麼不忌諱談論「變老」、「死亡」?因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從我出生的那一刻,我便與它們在一起,在有限的時光裡,我們可以活出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死後會去哪裡呢?靈魂真的存在嗎?
人總是在問一樣的問題,因為活人永遠沒辦法去驗證,當機會來臨時,也沒辦法「再活一次」去說明。
生活的隙縫裡藏著我們的希望與失落,卻可能在你無法掌握的片刻間,一筆勾銷、煙消雲散。獲得的掌聲、悔恨的淚水,歲月的美麗與哀愁,都會消失在夢幻泡影中......在人世間無論愛與不愛,捨得或捨不得,成就與否,最終都只能放手。
每一位親人離世,我總是認為他們飛往宇宙某個未知的空間裡,那裡有靜謐的銀河,他們繼續另一段旅程,「永生」的想法讓我不為他們感到惋惜,也不為自己感到遺憾。
「我真的活得好痛苦。」那是我六歲那年,二伯父從醫院「逃」回家對我說的話。
他是大家口中的老好人,也是容易在小說裡看到的,抵抗不了宿命安排的小人物。身受先天性疾病影響,個子長得矮小,個性溫和又可靠,終身未婚的他,視人為己、極講義氣,也很寵愛我們小孩們,盡量滿足我們任性的要求。
印象裡,二伯經常喊身體疼,我便與哥哥們輪流替他按摩。五、六歲的手臂想來是沒有什麼力氣,喜愛小孩的他,只是想要我們經常在他身邊撒嬌。
當病情陷入末期後,我們就很難得能看到他了,他在遙遠的醫院裡與病魔抗爭,除非,他又逃回家了。
有天爸爸接到電話,醫院打來說,二伯的病床上空無一人。爸爸和其他親戚也又去找我二伯,而我打開我的房間,燈沒開,隱約看到二伯就在窩在床角,他氣若游絲地對我說:
「阿妹,我真的活得好痛苦,我不想回醫院了。」他的神情一直烙印在我腦海裡。
二伯在醫院接受什麼治療,我不知道,為什麼二伯要對我說這些話,我也不了解。只是在他過世後,我不覺得難過。

用微笑和祝福做最後的告別
在葬禮時,每一位親人和朋友無不神情哀戚、悲傷落淚,我的奶奶更是一度衝過來呼天搶地(傳統習俗裡,白髮人不能送黑髮人),任何人都沈浸在深深的悲痛中,念及他的好而無法割捨。
也許現場只有我,滿懷著欣喜,我甚至一度要躲在廁所裡,我掩飾不了我的笑意(有陣子我也深受此罪惡感自責:我應該跟大家一樣哭才對)。
在蓋棺時,我記得我和我二伯說的話:
「你再也不用痛了,你的生命結束了,你離開這個飽受折磨的軀體,你自由了!我衷心地祝福你到更好的世界去。」
後來,我從未夢過他,他已經全然地從我的世界中離開了,我相信,他真的解脫了。往後的幾年,還是有二伯的朋友陸續來找他,聽聞他過世後,和我說:「過去承蒙他的照顧,沒想到來不及報答,他就過世了。」而後在他的遺像前,深深地一鞠躬。
當時我年紀太小,我們彼此的人生都參與得太少,二伯一生的故事,我沒資格書寫與評斷,也許在世俗的眼光裡,他可以說是命運多舛吧!但他總是急人之難、雪中送炭,自己情願餓肚子,也要分一半給其他「甘苦人」。這樣的他離開的,的確只是軀體而已,他分別在每個接觸過他的人身上,留下一些東西:
爸爸說,他會拒絕無效醫療,如果沒有機會,一定要「好走」;他的朋友說,感念他的善行,終於知道什麼叫真情;我知道死亡是必然的,可以頑強抵抗,或是微笑以對。
朋友問我,為什麼不忌諱談論「變老」、「死亡」?因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從我出生的那一刻,我便與它們在一起,在有限的時光裡,我們可以活出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6歲的純真、16歲的青澀、26歲的自立、36歲的成熟......一直到66歲、76歲,我們可以不活在別人的眼光裡,不讓別人決定我們,幾歲該有什麼樣子。那麼,你就能看見自己的美麗。
相反地,你越是恐懼,它越能占據你的心。
人生轉眼一瞬,為親人送別時,更能明白這道理。人身難得,要好好活;人生如戲,你玩得夠盡興嗎?
在最後一刻來臨前,提醒自己,要好好去愛。
本文轉載自《愛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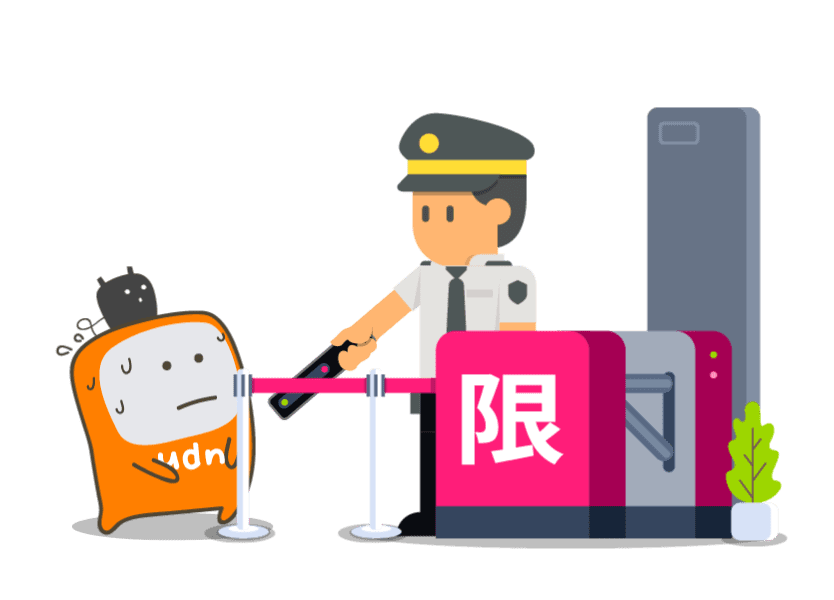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018%2Fcover.jpg%3F1758878794%3F17588787942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55%2Fcover.jpg%3F1755229041%3F175522904110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863%2Fconver.png%3F1752206769%3F1752206770102)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59%2Fconver.jpg%3F1748316292%3F17483162937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48%2Fcover.jpg%3F1754878820%3F17548788203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3%2Fconver.jpg%3F1748333976%3F1748333976770)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