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親耳聽見母親說:「如果我不值得活了,你要幫助我解脫。」該如何抉擇?「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面對「送母遠行」的生死之約,最後一段旅程該如何陪伴;當生命僅餘痛苦,人們是否有自主善終 的權利!《斷食善終——送母遠行,學習面對死亡的生命課題》精彩試閱:
自主善終的抉擇
母親在發病之初就囑咐,她若情況很糟,要幫助她解脫,這事情我牢記在心,家人也都知道。我的長子也是醫師,阿嬤談到此話題,總是哄阿嬤:「我們會幫你的,這你不用擔心啦!」母親幾次向我轉述,我心裡知道沒有這麼單純,只能順勢安慰母親。
二○一九年母親的病況快速惡化,更頻繁的談起希望能夠早日解脫的心願。她從安樂死 議題的討論中,知道在台灣「醫師協助死亡」是違法的,因此傅達仁先生必須遠渡重洋到瑞士,才能合法的從醫師手中拿到藥物,一口一口喝下,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母親表達不要我們用違法的方式幫她解脫,但是苦惱於有什麼方式可以無痛苦的離開人世呢?
早在二○一四年我讀了中村仁一醫師著作的《大往生:最新進的醫療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終點》,在這本書裡,我首次看見「斷食往生」這個名詞,有如在暗黑的隧道中看見了光。但我並未立刻告知母親此事。
中村醫師在中型醫院退休後轉往老人養護中心擔任專職醫師,在這樣的單位有許多「老衰死」的案例。他從一些跡象判斷老人已經接近臨終時,會通知家屬來送最後一程。
剛開始幾乎所有家屬,甚至是養護中心的同事都會提議:「那趕快送醫院吧!」他覺得很震驚:「這是什麼情況?」他的意思是:「送醫院做什麼呢?將死之人,不就是讓他安詳的走就好嗎?到醫院去做任何措施,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延長死亡的過程而已。難道大家忘了,我也是醫師,我懂得如何照顧臨終病人。」
有些家屬說:「那至少打個點滴吧!」他會倒一杯點滴請家屬喝,體驗點滴不過是加了一點葡萄糖的水。病人的全身器官已經失去功能,打了點滴,只是讓病人全身浮腫不舒服罷了!強迫臨終的病人進食,由於消化吸收功能也衰退了,只會造成腹脹、嘔吐等更大的痛苦。
病人不是因為沒有吃而死,是因為快要死了,吸收不了,所以才不吃的啊!經過反覆的解釋與實際操作,機構員工和家屬終於接受了中村醫師「什麼都不做,在養護中自然死亡」的作法。事實證明這種方式,臨終病人可以面目安詳、毫無痛苦的離開。若送到醫院,免不了進行一些無效的醫療,甚至被施與心肺復甦術,他稱這種受罪的死法叫做「醫療死」!
一般人常有病人臨終多日未進食,是「餓死」的誤解。中村醫師花了不少篇幅來說明「自然死」的過程與人體的反應。
自然死的實際狀況就是「飢餓」和「脫水」,一般來說,只要聽到「飢餓」和「脫水」,就覺得情況很悲慘,因為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明肚子很餓,卻沒有東西吃,或明明喉嚨很渴,卻沒有水喝,就像在沙漠裡迷路或漂流在大海上一樣,光是想像就覺得很痛苦。
但其實將死之際的「飢餓」和「脫水」,狀況並不相同,因為生命之火已經快要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一點也不會餓,也不會渴。「飢餓」時,腦內會分泌嗎啡物質,讓人充滿愉悅,也會有滿滿的幸福感。「脫水」時,會因為血液變濃稠的緣故,讓人意識指數降低,陷入朦朧的狀態。
強制人工營養法,來自醫護人員必須盡所有努力讓病人活著的使命感,以及家屬不能讓病患餓死,不能見死不救的罪惡感。而在這些觀念背後,隱藏了無法正視「死亡」這件事的態度。
中村醫師偏愛「自然死」而非「醫療死」。在他的生前意願書提到,不叫救護車、不插管、不用呼吸器等事項,因為擔心得到失智症而補充一點:雖然不易掌握準確的時機,最好趁自己完全癡呆之前,採取山折哲雄先生所提倡的「斷食往生法」。他自行整理出「斷五穀七天,斷十穀七天,吃木食(水果)七天,斷水分七天」的具體作法,其基本精神應該就是漸進式減少食物和水分的攝取,一個月左右就能無痛苦的往生。
中村醫師也提到美國在一九九○年和二○○五年分別有南希.克魯桑(Nancy Cruzan)和泰莉.夏佛(Terri Schiavo)兩位植物人,在家屬向法院提出申請獲准停止管灌餵食而往生的案例,兩位都是在停止灌食後兩週內死亡。
這讓我想起一九九○年我一位老師九十六歲,因為行動不便,每日只能待在房間裡,覺得生存沒有意義,因而在家中絕食離世的往事。老師是一位睿智而獨立的人,九十歲的時候,都還能夠自己搭車在台灣各地旅行,探望兒女子孫和學生。
可以理解,失去自由的他何以作此抉擇。但是聽到消息之初,還是非常不捨,覺得他被活活餓死,真是可憐。如今心中才感到釋然,原來他做了智慧的選擇,而斷食往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悲慘,絕對比在醫院「醫療死」好太多了。
二○一九年母親提起生命已無意義,痛苦難當,隨時可以離開。但苦於不知如何才能好死?我拿《大往生》一書請她閱讀。其實在那之前我已經多次輕描淡寫提到只要不進食,幾週內就會衰弱而亡。
譬如傅達仁安樂死新聞沸沸揚揚的時期,我曾說過他只要停止進食,就會往生了。我大阿姨已經快要一百歲,十幾年來一個人關在房間裡,電話中常常說日子很苦,佛陀怎麼還不來接她?我也跟母親提到阿姨只要不吃東西,就能解脫。但是,畢竟不是直系血親,不好提出這樣的建議。猜想阿姨也未必能接受這種方法。
母親讀完《大往生》,表情凝重的找我談話。她表示決定用斷食方式結束生命,時間就訂在次年的生日之後。我當時覺得太快,勸解她是否可以再延後一些。她說:「我這一生責任已了,沒有虧欠人,也沒有遺憾。現在不會做裁縫,只會吃飯、上廁所,凡事都要麻煩人,形同廢物。我活夠了,早點走,一定很快樂,沒有這裡痛那裡痛,也不用麻煩人家。」
看來母親想得很透徹,意志堅決。我答應她,我會全程陪伴,也會請教安寧照護專家,讓她平穩的離開。母親聽了如釋重負,鬆了一大口氣,露出欣慰的笑容,說她這下都沒煩惱了,可以開心倒數著過日子。我才驚覺,原來「如何離開?兒女是否放手讓她離開?」困擾著她已久。這是第一次,我體會到身為醫師,對母親有重大的意義。
接著我開始在網路、在書店尋找有關斷食往生的資訊,比較多的資料是探討自然死、安樂死、老衰死、平穩死,真正明確描述停止進食(禁食、絕食、斷食)得善終詳細過程的只找到海倫.聶爾玲(Helen Nearing)的《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Loving and Leaving the Good Life)。
海倫的先生史考特(Scout Nearing, 1883-1983)曾經是美國大學教授,是一位自由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思想家與行動家,晚年夫妻倆人放棄紐約的繁華生活,搬到佛蒙特州偏遠的鄉下,建造小規模的農家式住宅,過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他對死亡的看法也符合自然主義。
一九六三年(史考特八十歲)他在遺書寫下這些願望:
第一、當我病危時,我希望能順其自然地死亡。
(1)我希望能待在家裡—而不住在醫院裡。
(2)我不希望有醫師在場,他們既不懂得生命,又不懂得死亡。
(3)如有可能,我希望自己死在屋外的曠野上。
(4)在臨死前,我希望禁食,盡可能地不吃任何食物,也不喝任何飲料。
第二、我希望能清醒地體驗死亡的過程:
因此,不要用任何止痛劑或麻醉劑。
第三、我希望能盡快地、悄悄地死去,所以:
(1)不用注射點滴和強心劑,不需輸血、食物和氧氣。
(2)在場的人不用悲傷和遺憾,他們需要保持鎮靜,表示理解和喜悅,平靜地共同體驗死亡的過程。
(3)神祕現象的具體化亦是一個廣泛的經驗領域。我在活著的時候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力量,當我去世的時候,亦能滿懷希望。死亡既是一種過渡(transition)又是一種覺醒,他體現了生命過程的不同方面。
史考特的禁食死亡過程,海倫做了以下詳細的描述:
史考特在一百歲生日的前一個多月,與一群朋友圍桌吃飯時說:「我想我不能再吃飯了。」自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吃過固體食物,他有意識地選擇了離去的時間與方式,通過禁食的途徑來擺脫自己的軀體。禁食而死並不是一種暴力的自殺行為,它只是漸漸的消耗能量,平靜地、自覺自願地離開人世間的一種方法。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都做好了離開世間的準備。
我默許了史考特所採取的這一死亡方法。整整一個月,我只是在史考特要求喝果汁的時候,才給他一點蘋果汁、橘子汁、香蕉汁和葡萄汁。有的時候,他說:「我只想喝點水。」史考特沒有生什麼病,他的神智依然很清醒,他的身軀得到徹底的解放,只是他軀體內的生命力在逐漸的削弱。最後一個多星期,史考特只靠水在維持自己的生命,但他的軀體已經乾枯、萎縮,他隨時都可以安息長眠了。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坐在史考特的身旁,輕輕地督促他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我輕聲的對史考特說:「親愛的,您不用再留戀了,讓自己的身體隨著波浪向前飄去吧!您已經盡力度過了一個美好的人生,開始您的新生活,獲得新的陽光,我的愛將永遠跟隨著您。這裡的一切都將安然無恙。」
史考特的呼吸越來越微弱,越來越微弱,他漸漸的擺脫了自己的身軀,獲得了自由,就像樹上一片枯葉,隨風飄走了。「一切都好」(all....right),史考特輕微的鬆了一口氣,似乎在證明了萬物的正常運轉後才放心的離去。就這樣一個有形的人最終進入了一個無形的世界中。
中村醫師以科學和理性的角度描寫了自然死亡的無痛與安詳,海倫以智性和感性的筆觸描繪禁食而亡的平靜與自然。我在閱讀的過程中,體驗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再是令人恐懼、悲傷的,甚至可以欣然的去迎接,因為那是一個奔向自由的過程。
就這樣,我們母女做成了斷食善終的約定!

本文摘自《斷食善終——送母遠行,學習面對死亡的生命課題》,2022/03/31 麥田出版
│更多精選推薦↓↓↓
【橘世代課程】
陪伴您成為有趣而溫暖的大人》https://bit.ly/44stv2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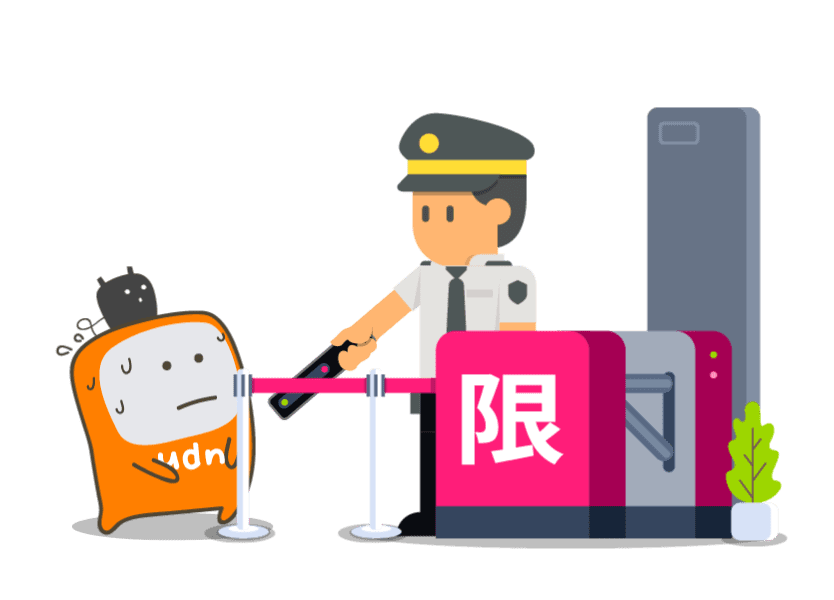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31%2Fcover.jpg%3F1768195717%3F1768195717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66%2Fcover.jpg%3F1769484812%3F1769484812853)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9%2Fconver.jpg%3F1748405683%3F174840568343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57%2Fcover.jpg%3F1769493574%3F1769493574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73%2Fcover.jpg%3F1769763032%3F176976303235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2%2Fconver.jpg%3F1748329564%3F1748329564308)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