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50歲提早退休,人生卻「暴跌」不掉速度陷阱,學「CASH」法穩定增值
-
「抗癌湯」真能逆轉癌症?猛喝恐住院!別一味跟著蕭萬長喝,防癌營養要這6種
-
每月「盲存」退休金事倍功半!掌握「所得替代率」月領5.8萬攻略揭曉
父親領公費念台北師範,畢業後,被日本台灣總督府派到廈門工作;家裡趕緊託人安排相親,帶母親赴任,徐文昭在廈門出生,念完小學,由日本恩師帶到台北...

每天觀看日本NHK電視新聞,是我多年來的習慣,半小時的報導內容讓我明瞭全球發生的大事。NHK播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聞中,烏克蘭人民命運悲慘最令人不忍;看著從戰地傳來的畫面,年輕時面對戰爭的驚恐場景,彷彿就在眼前。
1945年,美軍狂轟爛炸台北市,我逃過死劫,幸運生還。走上街頭,眼前卻盡是死傷,屍體橫陳,我熟悉的生活環境瞬間變成慘絕人寰的煉獄。已逾90歲、走過快要一個世紀的我,親身見識體驗過動亂時代下的悲劇,我絕對反戰,常常跟佛祖祈求世界和平,不要有戰爭。
出生於福建廈門的台北人
許徐文昭 是我的名字,許是夫姓,徐是娘家姓。母親於福建省廈門市生下我,時間是昭和4年、西元1929年、民國18年的2月24日(農曆1月10日),先夫許兆祥是屏東縣車城人,他是我一生可靠的伴侶,也都是信仰上的同修(註1)。
做為一個日治時代裡的台灣人,出生地卻不在殖民地台灣,身世與其他人略有不同,這中間的緣由,要從我的父母親婚配、爸媽兩方家族與父親生平講起。
父親徐榮宗是台北市人,他就讀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被政府(指日本政府)派到「國外」,對日本人而言,中國福建廈門是另一國度,對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又何嘗不是。
被派到廈門教書的父親,就好像遠赴國外工作,家裡人認為,與其單身赴任,不如趕緊娶個媳婦陪著一起過去,也多個人互相照料生活。

不知是時代造就著人們 還是人們被時代牽著鼻子走
當時的封建時代,婚姻常只是為繼承祖先香火以及繁衍後代,男女結合後綿延出子子孫孫,全都要遵從傳統;能有後代可祭拜祖先,是過去婚配重要目的之一。我的父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透過媒婆介紹撮合,父親與來自嘉義新港的母親徐何絨成婚。素不相識的兩人成為夫妻,現代人覺得不可思議,而當時服從父母,憑媒妁之言結婚,就是社會普遍的現象。
1840年到1842年,中英之間發生鴉片戰爭,英國的船堅炮利,以武力逼著中國門戶洞開,鴉片也進到一般小民百姓家裡。大時代的小人物難免隨波逐流,我的家人也不例外;外曾祖母、祖父都曾吸食鴉片,可想而知,父親家裡不會有什麼錢,在家排行老二的他,除了奉養父母外,還得供應唯一的弟弟讀醫學院。爸爸只能用日本政府公費唸師範學校,畢業後,父親奉台灣總督府派令到廈門工作。
日本恩師帶我到台北考中學 父贈筆盒成終生美好回憶
兒時,我在旭瀛書院上學,這是日本人在廈門設立的小學。日治時代,我們的學制與課程內容幾乎都比照日本,上小學一年級學日文的片假名,二年級念平假名,接著教九九乘法及跟日本有關的簡單歷史、地理。
日本統治台灣多年,部分日本人依然有歧視台灣人的情形。我在就讀的學校裡,深深感受到部分日本老師對「自己人」和台灣人差別待遇,但也有很善良的日本人,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還很有愛心。
我在書院經歷過三個老師,最後一位日本老師就是用真心及愛心教育我們,還會做課外輔導,小學還沒畢業前,他讓準備考中學的學生到家裡免費補習,師母也很歡迎我們,記得她還會特別端出點心招待大家。
小學畢業後,老師帶著我們大約20名台籍女生坐船到台灣,從基隆上岸,住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名古屋旅社,並陪著我們應試,考試通過後,還陪我們到台北中山女高報到。這位小學老師對學生很用心,我們對他的依賴很深,不像前兩位老師下班後喜歡飲酒作樂,心思都沒放在學生身上。
日本人撤離台灣,小學老師跟我們之間斷了音訊,但師生及同學感情甚篤,一旦重新找到老師後,常常聯繫,每年日本及台灣的學生都會幫老師慶生,我還曾經邀請他來台灣玩,這一位盡責的良師小栗常壽到高壽一百歲才離世。
小學畢業後來台灣之前,父親買了鉛筆盒送我,這令我非常開心。收到禮物那一剎那,好像踏進彩色華麗的世界裡,童年回憶中,從未感受到如此興奮的情緒。自此之後,我離開父母,在台灣就讀中山女高,似乎一下子就脫離童年,鉛筆盒就像來自父親的一份成年禮。
(註1)同修:佛門修行人相互的稱呼,指互相學習、參悟、指正、督促及相互鼓勵,在一起精進唸佛,共同進步,類似學校裡同學。許徐文昭與先生許兆祥都是虔誠佛教徒,因此稱自己丈夫為「同修」。(下一篇:隻身在台北住校的中學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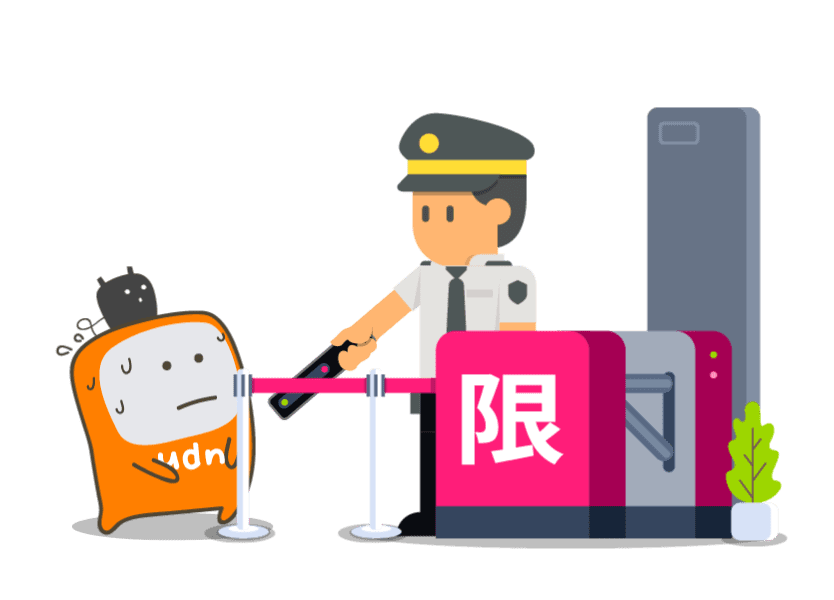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018%2Fcover.jpg%3F1758878794%3F17588787942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55%2Fcover.jpg%3F1755229041%3F175522904110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863%2Fconver.png%3F1752206769%3F1752206770102)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59%2Fconver.jpg%3F1748316292%3F17483162937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48%2Fcover.jpg%3F1754878820%3F17548788203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3%2Fconver.jpg%3F1748333976%3F1748333976770)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