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靠ETF存股無法財務自由!很多人忽略「2件事」辛苦20年白忙一場
-
住養生村身體變差會被趕走?75歲嬤花大錢「越住越不安」原因曝光
-
年輕時什麼都想要!最後把自己累垮…作家黃大米:中年後越能斷捨離,人就越自由
前年夏天,一個燠熱的午後,我牽著母親的手,推開了攝影社的玻璃門。還沒開口說話,正在吃泡麵的老闆娘抬起頭望向我們,而後說:「拍身心障礙手冊的相片嗎?」她的口吻聽起來很尋常,我的心臟卻被重擊了一下。原來,母親看起來已經如此明顯了。

那時候的她,因為水腦症與小中風引發失智,雖然我用盡一切力量來照顧她,卻無法改變她的失能,她不知道時間;無法分辨空間;說過的話與做過的事都不記得;她的目光遲滯,彷彿置身於另一個時空中。腦神經內科醫師對我說:「幫媽媽辦身心障礙手冊吧。這樣比較方便些。」
而又因為攝影社老闆娘的一句話,讓我決心申請「長照2.0 」。經過了一連串的訪視之後,母親像一個入學新生那樣,被安排了屬於她的課程。有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每週到家裡為她上一次課,原本整天只想躺在床上、肌肉迅速流失的母親,可以做許多運動了;原本提起筆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的她,能夠好好簽下自己的名字了。不久,我們又報名了社區整合照顧服務站「石頭湯」課程,每個星期一去服務站上音樂律動課。
一個班有十位長輩,第一次上課時的場面,令我感到驚訝和悲觀。原來,並不是所有的長輩都像我的母親這麼期待上課,有坐著輪椅而來的長輩,因為中風,身體不方便,根本不想留在這裡,滿臉不樂意的拍打著陪同者,想要離開。也有一開始就暴走的長輩,大聲呼喝,怒氣沖沖,揮舞著拳頭,不願坐下來上課。
可是,個子不高大、能量卻很充足的劉翠蘭老師真是個鋼鐵玫瑰,她不為所動的帶領大家唱著<茉莉花>,一邊使用道具律動身體。一小時的課程結束後,母親閃亮著笑容,說下星期還要來。
這是為輕微失智的長輩設計的課程,劉老師雖然年輕,卻很有耐心,懂得如何鼓勵長輩,引導他們回答問題、開口歌唱、協調肢體。之前不想上課的長輩還是繼續來上課,他們臉上的愁怒已經被柔和的喜樂所取代。
下起滂沱大雨的那一天,長輩們雖然都淋溼了,還是陸續到班上報到。當坐著輪椅、穿著雨衣的長輩也出現時,現場響起熱烈掌聲,我為自己的悲觀感到慚愧。
劉老師曾經是鋼琴老師,她如今彈奏的,是因疲憊與迷失而喑啞的靈魂之弦,這些靈魂甦醒,發出動人的明亮樂聲。
我一直試圖將自己的手從媽媽的掌中掙脫出來,邁開步子向前奔跑,只有六、七歲的我,對於上學這樣的事總是迫不及待。可是媽媽把我攢得緊緊的,絲毫不肯放鬆,她總是有很多的顧慮,擔心突然有車子疾馳而過,擔心巷子裡衝出失控的大狗。快到校門口時,終於成功滑脫了媽媽汗溼的手,往前奔跑了一段路,然後回頭看著她有些無奈的快步走來。其實到這裡,送我上學這件事也就差不多了,她會讓我自己走進校門;而且不久之後,因為在家裡從事育嬰工作,她再也沒有送我上學了。
五十年後,我們再度牽著手去上學。這一回,媽媽是學生,我成了家長。媽媽依然把我的手攢得緊緊的。

我們每星期要走一段路到社區整合照顧服務站,去上為輕微失智者開設的音樂律動課。自從媽媽因水腦症而有了失智狀況,我們度過了幾個月的艱苦時光,起初是家中成員無法接受,為什麼一個人突然就搞不清楚白天晚上了?為什麼同樣的話一說再說,同樣的事不斷糾結?應該喝水卻不喝水,吃過飯了還嚷著餓?
父親覺得老婆變了一個人,不知道該如何相處;兒子覺得老媽可能中邪了,應該帶去驅魔;只有我是最淡定、最能面對現實的,因此,我不驚惶也不憤怒,唯有憂傷。
我知道媽媽困在茫然無邊際的迷霧中,連自己也找不到,又如何能要求她顧慮到家人的感受呢?
「她簡直就是不可理喻。」
「她根本不願意溝通,給我裝傻。好啊,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跟她溝通,她的事不要來煩我。」
在這些焦躁的抱怨話語中,我沉默。只是走進迷霧裡,為她安排座椅休息;為她留下許多線索和謎底,讓她不致繼續沉落。有時候就只是留在她身邊,讓她感覺自己不是孤獨的。
當我申請了「長照2.0」,那真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媽媽從每天賴床不起到期待課程,遇見許多老師、志工和同學,她能完成自己的藝術作品,找到一群新姐妹,開心的唱歌跳舞,各方面的功能都恢復得愈來愈好。
對失智者來說,雖然沒有藥物能治癒,但我相信,接觸人群、從事團體活動、找到自己的興趣,對於認知與生活趣味都有很大的幫助。
看著長者們在台上表演,我用力鼓掌,把手都拍疼了。牽著媽媽的手去上學的每一天,我都覺得很感激,因為不知道能送到哪一天,所以格外珍惜。
本文摘自《以我之名:寫給獨一無二的自己》,天下文化 2020/03/31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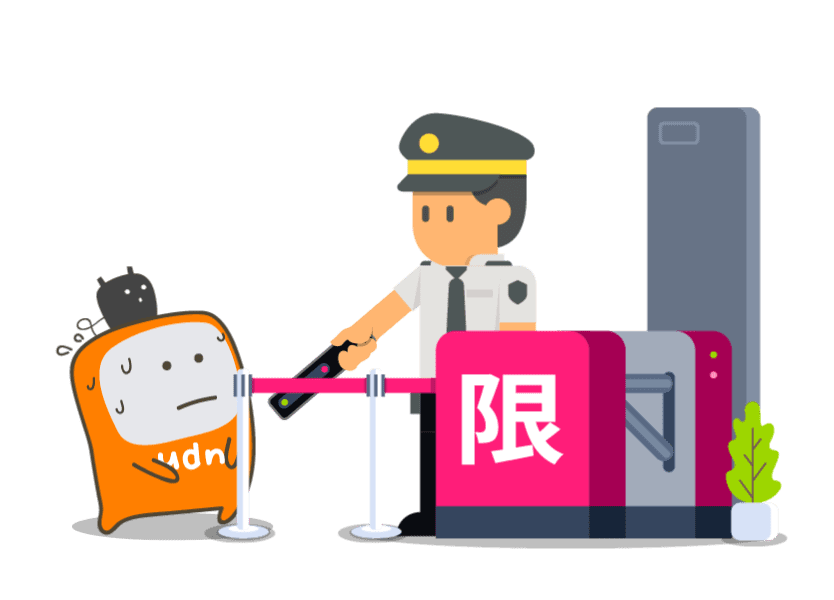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018%2Fcover.jpg%3F1758878794%3F17588787942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55%2Fcover.jpg%3F1755229041%3F175522904110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863%2Fconver.png%3F1752206769%3F1752206770102)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59%2Fconver.jpg%3F1748316292%3F17483162937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48%2Fcover.jpg%3F1754878820%3F17548788203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3%2Fconver.jpg%3F1748333976%3F1748333976770)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