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50歲提早退休,人生卻「暴跌」不掉速度陷阱,學「CASH」法穩定增值
-
「抗癌湯」真能逆轉癌症?猛喝恐住院!別一味跟著蕭萬長喝,防癌營養要這6種
-
每月「盲存」退休金事倍功半!掌握「所得替代率」月領5.8萬攻略揭曉
一場大病,讓陳文茜 明白,生命輕如雲。我們的一生都是回不去的進行式,如果好好想著愛,就不用怕凋零。關於愛,關於生命,關於你,關於我,陳文茜畢生最深情的一次書寫。《終於,還是愛了》與愛情教主張小嫻 筆談摘錄:
願我走的時候,心如星空
疾病,是我一生的朋友。死亡,是我熟悉的路人,我和它擦肩而過已太多次。我不會奢望自己還有「十年」歲月,我的目送,是對自己生命旅程最後的目送。

我想的不是如何布展我的喪禮,那已經與我無關。
我明白歲月不斷加添我的疾病,過去我一次又一次從鬼門關前溜了。但總有一天,我會被它抓住,我不會一直那麼幸運。
所有童話的結尾處,都布設了謎語。有的殘酷,有的令人迷醉。我自2013年起,年年住院,年年動大刀,康復愈來愈慢。
我剩餘的人生,正如童話故事中的兩種結局。一個知道自己老了,修鍊靈魂,靜心等待死亡。
另一個態度:我離插管、敗血、尿袋、昏迷的狀態還有很長的路,還很遠。是的,我年長了,老了,大病了,但我仍可以抓著一定的青春心態,逆襲人生。
至少最後一夜前,我要活得如飛舞彩蝶,絕不哭倒在露濕台階。我本不是石塊,何必隨著時光沉落。
小嫻,妳曾閱讀德裔美籍作家塞繆爾‧厄爾曼(Samuel Ullman)七十多年前寫了一篇只有四百多字的短文〈青春〉(Youth)嗎?
它首次發表立即引起轟動,讀者們把它抄下來當座右銘收藏,喊著「老兵不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指揮太平洋戰爭期間,辦公桌上也始終擺著〈青春〉影本的鏡框。其中一段:
「青春,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矯健。它是心靈的一種狀態,是頭腦的一個意念,是理性思維的創造潛力,是情感的勃勃朝氣,是人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青春,意味著甘願放棄舒適去闖蕩生活,意味著超越羞澀、超越怯懦的膽識與氣質。所以六十歲的男人可能比二十歲的小夥子,更擁有這種膽識與氣質。沒有人僅僅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變得衰老。
人只是隨著理想的毀滅,才出現了老人。歲月可以在皮膚上留下皺紋,卻無法為靈魂刻上一絲痕跡。憂慮、恐懼、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僂於時間的塵埃中。
無論是六十歲還是十六歲,每個人都可以被未來所吸引,都可以對人生路途中的歡樂,懷著孩子般無窮無盡的渴望,奔跑。」
我喜歡這段話,因為它一語道破了組成「老」這個字的充分條件。它不是表面的年齡,它是對渴望勇敢地追求,對恐懼一腳踢開的魄力,它是回到孩子般的純真,並且具備膽識地與時光同行。
既然我已看見生命之波最後的幾片玫瑰花瓣,我想告訴過往飛逝的年華:去吧!不斷地去吧!抱歉,我從此不再理你。過往,只是記憶。不是滄桑,不是傷痕,更非衰老!
我在心頭種了一朵青春的鮮花,誰也別想摘掉!
我不會否認歲月有灰燼,但我的靈魂還有火焰!
我不會無視歲月殘痕,但我的心仍有等待!
當我病了,老了,人世間所有的聚散離合難免會有一點感傷。它帶著一點滄涼,帶著一絲柔情,也帶著年輕時候不能明白的急切。就這樣嗎?我將帶著這些遺憾,筆直、冷靜、無聊地走向死亡嗎?
親愛的小嫻,大病一年之後,領了什麼「重大傷病證明卡」,我更不願被感傷淹沒,不願向歲月折服。
我告訴自己去愛吧,像沒有明天的去愛。去告白吧,丟掉渾身練就的武裝尊嚴,去告白吧。因為我的明年、我的後年……可能再也沒有機會這樣做。
它當然可能毫無結局,但誰又要結局呢?
因為人生真正的結局是死亡,是告別。
在告別之前,塵世中,找一個人,或找幾個知心朋友相依相伴,終究是幸福的。
小嫻,這是你的一段話:夢,很遠沒關係,仰望夢想也是幸福。
我仰望滿天星斗,那裡有已經死亡的星球,它們是千年前捎來的問候,閃爍著,欲語還休。那裡還有今夜剛剛升起的明月,柔情眷戀大地,也眷顧大地之上無以計數的我們。
只要抬頭仰望,月娘始終相伴。即使黑烏烏的雲朶遮住了她,我們也知道她永遠都在。李白的詩,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
當我病了,老了,我比四十、 五十歲的我更相信青春。把哀嘆憂愁,留給不知生命時時刻刻逝去的中年人吧。
當我病了,老了,我想在心裡保留一個地方,獨自呆在那兒,讓我可以在那裡愛,即便不知道愛什麼,不知道愛誰,也不知道怎麼愛,愛多久。
但我要學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而且唱著I Am Every Woman,我是每一個不同年齡女人的組合。我的心中永遠保留一個等待的地方,別人知不知道,領不領情,無所謂。至少我不是未死之前,已成僵屍,筆直地走向死亡的女人。
我仍要等待愛,不是為了愛誰。因為我等的是它:愛,而不是一個特定的人。
我不會虛度最後的年華,我的生命已經褪色,生命很快地就會拋棄我。不需要我自己多添柴火,加速它的燃燒滅亡。
在我成為灰燼之前,我將擁抱一切,如擁抱滿天星斗。
願我走的時候,往事如星空,心也如星空。最後我看到的光,不是一片黑暗,而是閃閃發亮的星斗。
本文摘自《終於,還是愛了》,有鹿文化 2020/06/05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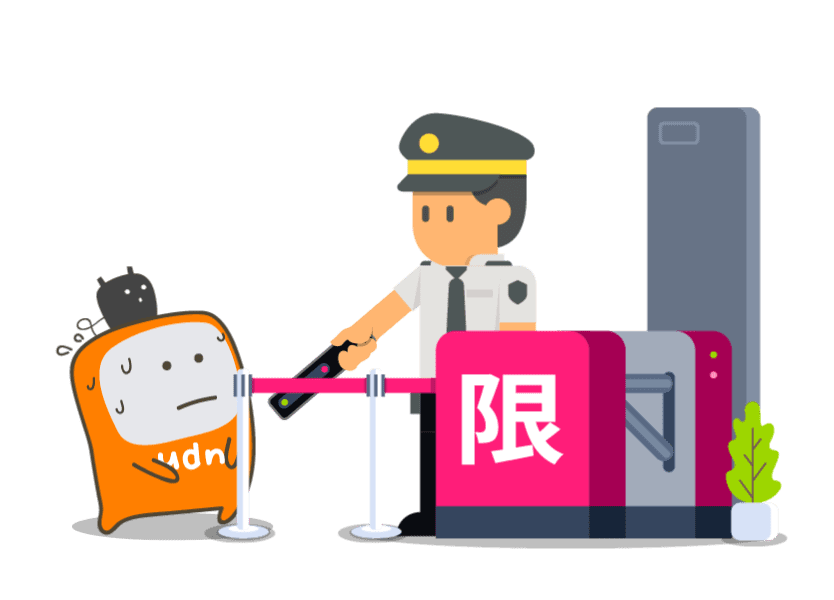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018%2Fcover.jpg%3F1758878794%3F17588787942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55%2Fcover.jpg%3F1755229041%3F175522904110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863%2Fconver.png%3F1752206769%3F1752206770102)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59%2Fconver.jpg%3F1748316292%3F17483162937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48%2Fcover.jpg%3F1754878820%3F17548788203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3%2Fconver.jpg%3F1748333976%3F1748333976770)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