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朱全斌
【朱全斌-人生經驗過多種角色:電視製作人、紀錄片導演、編劇、作家、廣播主持人等,去年卸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院長一職,從職場退休,展開退休新人生。】

記得大約在10年前,有一天在同事的退休送別會上,聽到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我終於可以做自己了。」
是的,職場常常讓我們不能做自己,尤其對受僱於機構的上班族來說,他們工作的累,往往不在工作本身,而在於需要跟他人謀和。
聰明才智固然重要,跟同事之間相處的情商更重要。上班讓我們感到不自由是因為內在自我經常受到了「組織我」的壓抑,每個職位都有相對應的工作規範與倫理,我們不一定都認同,但是都需要遵守。
然而,人是慣性的動物,安穩的職位讓我們有如被豢養的動物,久而久之,那不受控的本性漸漸被馴服了,因而等到退休那一刻到來,可以完全自組織的藩籬脫離時,反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身體還算健康的情況下,退休人士的生活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快快樂樂地開啟生命新的一頁,到處旅行、玩耍,或是投入自己的嗜好,跟老朋友、老同學恢復聯絡,經常聚會,或是忙著學習與發展新的興趣。很多剛退休的人都會經過這一段。
另外一種則是對閒下來的狀態很不習慣,想要繼續擔負責任,或者保持生產力。他們也許會在原工作單位從全職改成兼職,或者試圖尋找一份新的工作。不少人會幫兒女帶孫子,或是去做義工,也有為了繼續有收入,而將精力投注在股票、理財等事務上。
這兩種人代表著對人生持享樂或生產的基本態度差異。而實際上,有更多的人是在兩者之間擺盪。
當他們還在工作時,總是期盼著假期的到來,而退休後不必再上班,餘生都可以用來度假了,卻又會捨不得放下工作。這有點像是鐘擺效應,君不見許多一退休就忙著玩樂的人,三、四年之後,也玩得有點乏了,又會想找個事做。
會形成這樣的矛盾是因為在機構待久了,「組織我」成為我們對自我的主要認知,我們關心的事務、思考模式、價值觀甚至世界觀都受到它的影響,我們透過組織得到存在感,長期養成將組織看得比個人重要的習慣,組織內的表現、升遷、待遇與人際關係也成為念茲在茲的人生目標與動機,一旦卸下了職位,失去了努力的方向,還真的有些茫然呢。
因此問題不在於選擇享樂或者繼續生產,畢竟,享樂或生產都只是外在的表象,不該是我們人生的目的。退休後人生的時間越過越少,是否能掌控方向,好好把握這百分百屬於自己的日子,關鍵仍在於有沒有建立核心的價值觀。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符合他的價值觀,那他就是職場中的幸運人,因為這不只是一份謀生的工作,還是能讓他實踐自我,甚至可以發揮個人稟賦的天職。對這樣的人來說,退休也許只是轉換工作形態或場域而已,不會因失去職位就同時也失去存在感。
例如企業家如果不只是為了牟利而工作,背後另有更高的利他動機,那只要是可以繼續幫助到別人,也一樣可以在非營利的領域中施展才能得到快樂;而像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人士,以往也許只為出得起費用的客戶工作,現在則可投身公益,幫助那些經濟弱勢族群,得到的成就感說不定比以往更大。
如果您沒有這麼幸運,知道自己的天份所在,卻大半生都為了生活而沒有勇敢去追尋夢想或栽培自己,那麼此時正是義無反顧該起步的時候了。
許多人到了人生可以完全做自己的時刻卻裹足不前,乃是因為他們沒有放下功利心,仍然會用「是不是太晚了?」「不會成功了吧?」這樣的顧慮來否定自己,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退休生活 最可貴的就是可以完全自在,不必再考慮他人的眼光或評價,自己過什麼樣的日子自己決定,除非是沒有天份,否則我相信去做能激發自己熱情的任何事都會是快樂的。
我今年開始了我的退休生活,我發現自己心態上最大的改變就是沒有了得失心,不再用目標管理主導我的生活。雖然我仍有想要完成的事,卻並不執著於它的進度與成果。我每天都問自己的內心,當天把時間做怎樣的分配可以令自己最開心?
這是我生命的最後一段,我要讓它完全屬於我,同樣有玩樂也有生產,卻不必再受制於人,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來進行,在心與價值觀的帶引下,得到自然的平衡。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富足的人生。
本文摘自《安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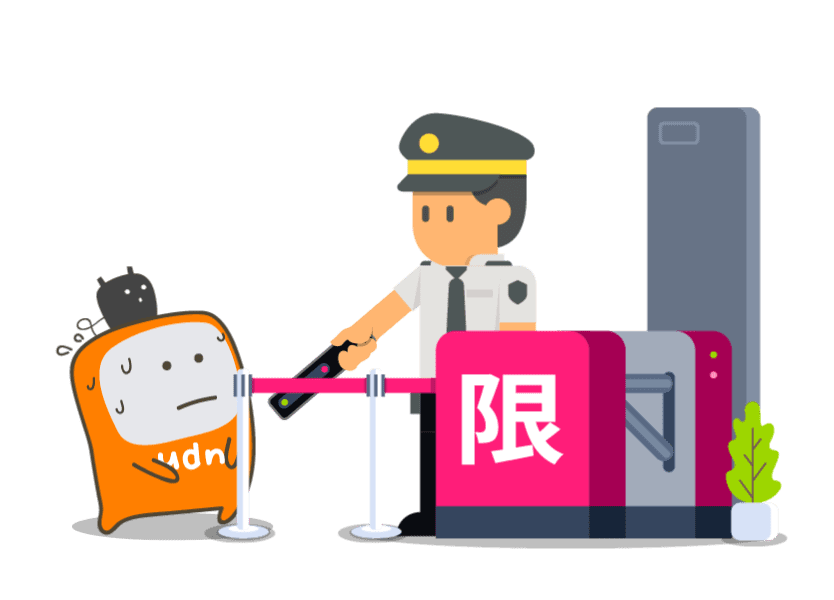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31%2Fcover.jpg%3F1768195717%3F1768195717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66%2Fcover.jpg%3F1769484812%3F1769484812853)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9%2Fconver.jpg%3F1748405683%3F174840568343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57%2Fcover.jpg%3F1769493574%3F1769493574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73%2Fcover.jpg%3F1769763032%3F176976303235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2%2Fconver.jpg%3F1748329564%3F1748329564308)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