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亞隆,存在心理治療大師,以治療死亡焦慮著稱,卻在得知愛妻瑪莉蓮罹患癌症、來日不多的當下,也一時無法承受,萌生隨她而去的念頭。
「我們應該合寫一本書。」瑪莉蓮鄭重其事地對丈夫說:「把我們所面對的困難記錄下來,對其他遇到類似狀況的人來說,或許會有點用處。」

在歐文‧亞隆的治療經驗中,人活得越充實,面對死亡就越坦然。但末期病痛日復一日的折磨、丟下伴侶的錐心之痛,不論是要走的人,或留下的人,都難以釋懷。最後瑪莉蓮選擇合法輔助自殺,他更是震驚又害怕,不願放手。
當治療師成了當事人,該如何與絕望相抗?又該如何有意義地活至最後一刻?以下是歐文‧亞隆在喪偶 後寫下的文章:
出殯的日子。墓園就在四個孩子都念過的岡恩高中﹝Gunn High School﹞對街,從家步行約二十五分鐘。此刻寫下這些,離瑪莉蓮過世雖然沒有幾日,可葬禮的細節大多都記不真切了,我還得去問孩子及朋友才行。創傷壓抑:另一種有趣的心理現象,以前聽許多病人講過,自己卻從未經歷過。
這裡,我寫的只是自己還記得清的。有人載我到墓園禮拜堂﹝不記得是誰了──但我想應該是女兒,一整天下來,她都前前後後跟著﹞。我們提早十分鐘到達,依稀記得,寬敞的禮拜堂裡已經滿滿是人。拉比派翠西亞‧卡林-紐曼揭開儀式序幕。她和我們是舊識,數年前還曾邀請瑪莉蓮和我到史丹佛希列爾堂﹝Hillel House﹞講演。
三個孩子﹝班恩、伊娃及里德﹞和兩位最要好的朋友﹝海倫‧布勞及大衛‧史皮格爾﹞分別簡短致悼詞。我清楚記得,五個人的表現無不細膩動人。兒子里德講的尤其令我刮目相看。他玩了大半輩子相機,是個優秀的攝影家,但直到去年,他拿他寫的詩及散文給我看,都是有關他童年及青少年的,很明顯地,極有才華,近來還頗有佳作。但葬禮過程我也只記得這些了。記憶中的事抹淨得如此徹底﹝或無法記錄下來﹞,生平還是頭一遭。

接下來記得的是,自己坐在墓園門外,我是怎麼從靈堂來到這兒的?走路?還是坐車?不記得了。後來問女兒,她說她和我一起走過來的。墓園裡的事倒是記得,面對瑪莉蓮的棺木,我和孩子們坐在前面第一排座椅上,棺木緩緩降入一個深坑,不過幾呎遠,就是她母親的墳。
坐在霧中,一動不動,有如雕像,這我記得。但當禱告聲揚起,所有來賓圍繞墓穴排成一列,每個人輪流剷一鏟土拋到棺木上,記憶中就只有模糊的印象了。之所以還記得這項傳統,是因為我參加過別人的葬禮。至於那天,我整個人嚇呆了,要我往瑪莉蓮棺木上剷土,我做不到。因此,就只是坐著,陷入昏沉狀態,直至每個人都做完為止。我沒有加入埋葬瑪莉蓮的行列,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如果有人注意到了,希望他們將之歸因於我的站立不穩及高度依賴拐杖才好。過沒多久,隨著孩子們,我回家。
在家裡,許多參加葬禮的人──或許是絕大部分──都來了,大家聊天,飲香檳,享用孩子們請來的外燴師傅準備的點心。我自己是否喝過或吃過什麼,不記得了。想起來,應該跟兩位要好的朋友說了許久的話,但同樣地,整個聚會的細節全都消失無蹤。有一事倒是確定的:我不是個稱職的主人,沒能走動招呼朋友們,事實上,我不記得自己有離開椅子過。兩位朋友坐我旁邊,談到史丹佛要開一門夜間課程,講授十九及二十世紀短篇小說,邀請我加入他們。
啊,好的,我會的,我決定。或許這代表我沒有瑪莉蓮的生活的開始。
但接下來,眨眼間,我又想起了地下棺木中的她。但我趕走這念頭;我知道,瑪莉蓮並不在她的棺木中。她什麼地方都不在。她不再存在──只存在於我的記憶中,存在於許多愛她的人的記憶中。我會真正接受這一事實嗎?我會接受她的死亡,以及自己將要來臨的死亡嗎?
我無需獨自面對瑪莉蓮的死,葬禮後,四個孩子都陪著我,能陪多久就多久。女兒伊娃擺下婦產科醫師的工作,照顧我三個星期,體貼入微。最後,我跟她說,一個人過,我準備好了。但就在她要走的前一晚,我做了個夢,真正的夢魘,許多年來的第一次。時在午夜,暗黑深沉,我聽到門響,知道臥室門開了,望向門口,見一男子的頭,相貌英俊,戴一頂深灰軟呢帽。也不知為什麼,我知道他是幫派分子,也知道他是要來取我性命的。醒來,心跳如擂。
這夢明顯告訴我,我自己不久也要赴死亡之約了。灰軟呢帽……父親就是戴頂那樣的灰軟呢帽。父親也是相貌英俊。但絕不是幫派分子。他溫文有禮,過世四十年了。怎麼會夢到父親呢?我很少想念他。又或許,他不是來取我性命,而是來護送我前往冥間,去那個和瑪莉蓮常相廝守的地方。
也或許,這夢是告訴我,我還沒為女兒的離去做好準備,還沒準備好自己一個人過。但我沒把這夢跟她說:畢竟她是醫師,已經取消了許多病人的約診,該是讓她回去過自己生活的時候了。兒子里德倒似明白我還沒準備好一個人過,也沒問我,周末人就來了。我們痛快地下了許多盤棋,一如他還是孩子時。
瑪莉蓮去世下個星期才滿月,我已經一個人過了第一個周末。回想瑪莉蓮的葬禮,我驚訝於自己那天的麻木及平靜。或許是因為她臨死時我一直都陪在她身邊,該做的我都做了。我始終守著她,數到她的最後一口呼吸。還有那最後一吻,在她冰冷的頰上──那才是真正道別的時刻。
本文摘自《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2021/05/01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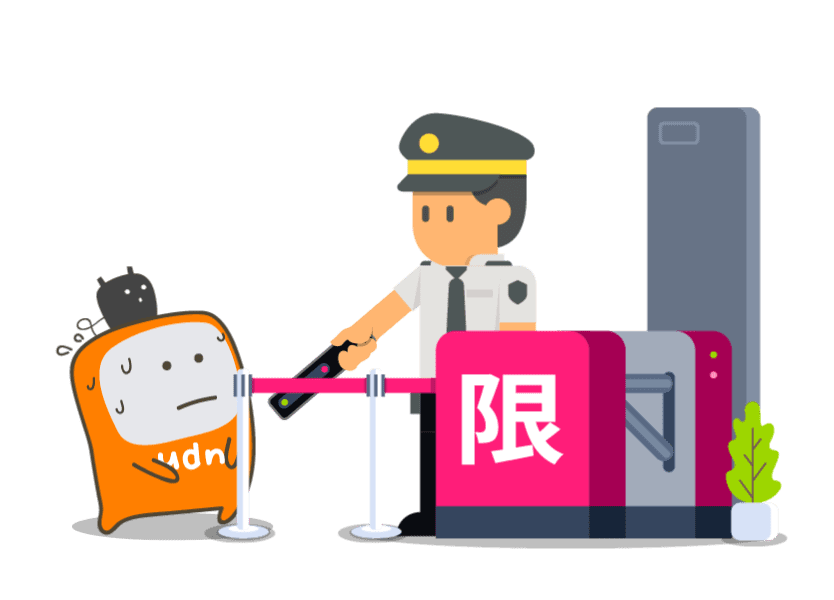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31%2Fcover.jpg%3F1768195717%3F1768195717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66%2Fcover.jpg%3F1769484812%3F1769484812853)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9%2Fconver.jpg%3F1748405683%3F174840568343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57%2Fcover.jpg%3F1769493574%3F1769493574201)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173%2Fcover.jpg%3F1769763032%3F1769763032355)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2%2Fconver.jpg%3F1748329564%3F1748329564308)





















udn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