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靠ETF存股無法財務自由!很多人忽略「2件事」辛苦20年白忙一場
-
住養生村身體變差會被趕走?75歲嬤花大錢「越住越不安」原因曝光
-
年輕時什麼都想要!最後把自己累垮…作家黃大米:中年後越能斷捨離,人就越自由
三毛親侄女,雙胞胎中的妹妹陳天慈 ,也是三毛筆下那個「特別的天使」。在三毛逝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我的姑姑三毛》一書,以22篇回憶性質的散文,回憶幼時和姑姑一起生活的日子......
1979年,全家人一起去機場接從西班牙搬回臺灣的小姑,只記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那麼擁擠鬧騰的場面。爸媽拉著剛上小學的我和姐姐,整個現場鬧哄哄的。我記得以我當時的身高,眼前高度就是那些機場裡用來分隔人群的紅色絨布線和可伸縮繩子的柵欄,而且其中很多都被推倒了。
一堆男人穿著西裝褲的腳,還有女人為了工作在這種場合還要穿高跟鞋的腳,跑來跑去,匆忙而謹慎,雜亂又嚴陣以待。也不知道他們在嚷嚷著什麼,好多人拿著攝像機,當時沒有無線麥克風,都得拖著好長的電線。當時還小的我生怕被電線纏住,緊緊抓著媽媽的手。雖然不確定是什麼事,但我直覺家裡出事了,遠方的那位小姑要回來了。
這些人都是記者,個個神情緊張,好像等著獵物出洞,然後張牙舞爪地撲上去。我們家人也在等候,卻感覺到不同氛圍,更多的是懸在空中的擔心和準備好保護小姑順利出關的架勢,本來流動性很強的機場,此時這群人卻聚集著停滯不前。兩軍對壘,我軍明顯兵力不足。
「來了嗎?那個帶帽子的女人是三毛嗎?」
「不是,那是個老外,你昨天沒睡好嗎?」
兩位男女記者就在旁邊說著。爸爸自言自語地說:「這場面,我們都看不到人了,小姑下飛機一定累壞了。你們兩個小的抓緊呀,別跑丟了,人太多了。」爸爸皺著眉頭,他總是容易緊張和不耐煩。我和姐姐如臨大敵,不敢出聲,緊緊跟著,小手緊緊被大人抓著。
我看著眼前穿著黑色西褲和黑皮鞋,不停踱步的腳,他每踱一次,我就得順著他的節奏閃躲那跟著移動的電線,以免自己被纏繞進去。孩子的視角和記憶總停留在一些不相關的小事和小畫面上,卻記憶猶新。
不知道等了多久,小姑終於出來了。她拿著紙巾,掩著臉,不知道是在哭還是因為剛下飛機很累。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有計劃地將她層層包圍,密不透風,包括本來在我眼前的那雙腳,他的電線在混亂中居然也沒纏上任何人,專業素養也是了得。小姑憔悴的臉被無情地湊上來的一堆麥克風團團圍住,對肚子早就很餓的我來說,這看起來像很多層的冰棒,小姑卻顯然不太喜歡。
「三毛,三毛,能否聊聊你現在的心情?」
「能談談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嗎?」
「你打算回來長住嗎?」
一堆聲音好像交響樂,分好多聲部,和諧又不衝突地此起彼落,旁邊一支支的麥克風以小姑為圓心,整齊劃一地用同一速度向同一個方向前進。荷西走後,小姑回臺,是如此獨自面對同胞的慰問。小姑一句也沒回答,我那高大的老爸一手抱住小姑,一手還抓著快被懸空提起的我姐姐,快步朝機場入境大門走去。媽媽牽著我和其他家人在後面追著,我拼命跑著,也顧不得那雙小心翼翼保護很久的全新白色球鞋不知被誰狠狠踩了一大腳了,小心思在想早知道今天應該穿姐姐的鞋。

小姑回來了,回到成長的地方,家人的身邊,帶著那顆突然被掏空的心。在後來的變故中,爺爺奶奶到西班牙的旅程也少被提起,大人都忙著處理後事和擔心小姑的創傷。從機場回到奶奶家後,小姑被安置到安靜的房間。
為了讓小姑好好休息,小孩們也被再三告知不要打擾,雖然過了幾天後,我們就已經完全把這叮嚀拋到腦後了。我們小孩對從那麼遠的地球另一頭回來的小姑可是非常好奇的。那個遙遠的地方住著什麼人,他們吃什麼,玩什麼,看什麼卡通,玩橡皮筋跳繩還是無敵鐵金剛?我們有好多問題想問小姑,索性每天去小姑房門外張望偷看,趴在門底的縫外偷聽。兩個小孩窸窸窣窣以為別人聽不到,這是一種孩子的天性,一種孩子獨特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知道看著看著門就會自動開了,等著等著裡面的人就會自己走出來。
「天恩天慈,你們在幹嗎?等小姑呀?」小姑還是出房門了,看起來很累。
「小姑,我們在看你。你會說外國話呀?」我怯生生地說道。剛剛回家的家人對小孩來說還有點陌生。
「你有沒有騎過駱駝?」姐姐也鼓起勇氣問道。
當時我們只知道這位洋小姑有很不開心的事,全家人雖然關心她,也不敢多問,給她太多壓力。但是這種氣氛,反而讓小孩都感受到說不出的不對勁兒。說完不等小姑回答,我們就衝進小姑房間。一個一直想進去卻不被允許的新天地,一位新夥伴, 只是房間裡少了一顆放在撒哈拉沙漠忘了帶回來的心。
一進去是一個玄關,正面是洗手間,左邊是臥室,右邊是小客廳。左邊小姑的臥室擺設很簡約,長條形的空間,進門邊上放著面對牆的木頭書桌,桌上沒有太多東西,可能是因為剛回國的關係,地上還堆著還沒整理好的行李。把放在地上的床墊當床,是小姑一向喜歡的風格,靠牆那邊還有矮書架,上頭放滿的書倒不像是剛回國的人的書架。房裡的香味是我不曾聞過的異國情調,神祕而親切。床上還有很多流蘇的披風,這要怎麼穿,搞不懂的時尚!我一屁股往床上坐下,把玩著小姑的床單,好像這房間什麼都很新鮮。
「你們今天不上課呀?」小姑問起。我們異口同聲說道:「放學了呀!」姐姐說完就跑到對面的小客廳,「砰」一聲把門打開。又是極其簡樸的設計,木頭的茶几,民俗風的小沙發和坐墊,又有一排矮書櫃,上面堆滿了皇冠雜誌和一些洋文書。紙糊的燈籠從天花板吊下來,黃色的燈光很溫暖,也有點黯-《我的姑姑三毛》序淡。
「小姑,小姑,我們可不可以睡在你這裡?」姐姐問起,跟著跑進來的我也一邊往地上坐,一邊附議。
「我們可以睡地上。小姑,你要不要也和我們睡一起?」我接著提出意見,自信地認為真是個美好夜晚的提議。「好呀,今天晚上我們三個人睡一起。誰要睡中間?」小姑終於有了點笑容。「我不要睡姐姐旁邊,她會踢我。」我趕快選好位置,也就是心想小姑能睡中間。那晚,一塊地板,三個孩子,兩個睡得很香,一個睜眼到天亮,伴著雨聲和想見卻見不到的月亮。
之後的一個午後,我在奶奶房間裡的櫃子上爬上爬下,奶奶走進來,我下意識地以為要被罵了。奶奶穿著深藍色的小旗袍,一張白手絹插在胸前布料交叉的縫裡。「怎麼會這樣?哎!還是不吃飯?」奶奶邊說著邊拿起手絹擦眼淚。我正爬在櫃子頂,不知所措地不敢說話。家裡的氣氛小孩是知道的,雖然幫不上忙,貢獻一雙小耳朵和無辜的眼神也是一種安慰吧!
奶奶走出房間後,我趕緊爬下來,輕手輕腳走到昨晚睡覺的小姑房門口。經過昨晚的敲門成功,這門終於是開著。我有點膽怯地叫了一聲「小姑!」還是害怕這天匍匐前進著偷看會不會被發現。小姑回了一句:「天恩還是天慈?」 小姑雖然當時正處在人生低谷,在難過中療傷,看到小孩還是帶著微笑回答,或者是不想嚇壞兩個每天在門外等候許久的小人影吧!
「進來。」 我和姐姐像等到芝麻開門的指令,其實又有點害羞地跳著衝進這個新天地。書桌上檯燈還是像昨晚一樣亮著,小姑用的圓珠筆和爸媽買給我們的都不同,小姑的字好隨意、好率性,這樣斜斜的字體肯定會被學校老師要求罰寫的,而且我看不懂那語言。
「小姑,你怎麼沒有橡皮擦?」 一句冷不防無厘頭的問話讓小姑笑了。「沒有呀,你們給我一個好嗎?」 小孩的心靈療法在這一刻自然地展開,沒有特定章法,沒有固定脈絡,只有一堆童言童語做成的調養祕方。上帝的巧思,大人養小孩,小孩也用他們的方式撫慰大人的無奈和壓力。我大聲地說:「那邊有個文具店有賣很多橡皮擦哦!」
橡皮擦,擦掉悲傷,擦掉奶奶和小姑的眼淚,然後再買幾支彩色鉛筆,畫上新的色彩和笑聲,創作出一幅新的畫。
「你一定是想讓小姑給你買那個爸爸不讓你買的自動鉛筆,我就知道。」小心思一下就被我姐無情地拆穿,雙胞胎哪個心裡想什麼壞主意都逃不過另一個的法眼。管他用什麼方法,反正小姑願意走出來就好。很可惜,第二天小姑還是沒和我們一起出門,還是選擇和我們在小客廳裡玩。
我們三人約好下次要去那家文具店,南京東路的小街道,從此多了三人手牽手齊步走的身影。想你想成的撒哈拉留在了遠方,天下掉下的沙還是沒越過太平洋。不起眼的童言童語在每天的日常中慢慢加溫,橡皮擦雖然擦不乾淨那年中秋夜的心碎,卻慢慢稀釋了悲傷,填補了缺口,用最天真無邪的方式。

-《我的姑姑三毛》序 我們懷念的您-
三毛一直是個幽默的人,她的荷西也有著西班牙人的熱情和風趣。他曾聽三毛說:「雨是天上下來的粉絲條。」聽到這,我小時候就常在想下大雨時張嘴就能吃飽吧!我倒覺得雨是情人發來的信息,總在你沒防備時發來,常常一發就好多條,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線準備好,他想發就發,有點任性和小調皮。敏感的人聽出其中的急切和渴望,熱戀的人聽出愛意和想念,三心二意的人聽出試探和懷疑。
三毛是重感情的人,在雨季裡寫出了年少的暗戀——《雨季不再來》,那種單純的喜歡和遠遠的欣賞,確實是現在來匆匆去匆匆的行程裡很奢侈的花費。今天的我在新年剛過的日常中,靜下來,聽到惆悵和懷念,這是每年都逃不過來自心底的情人信息 。
這就是我的小姑,你們認識的三毛,那個傳奇女作家,旅居他鄉的獨立女性。我從小認識的親人、玩伴,用獨特的方式帶領我成長的人。小姑如果在世,也有七十七歲了,雖然我們都很難想像那個留著兩個小辮子,說話輕聲輕語,勇敢追愛,充滿好奇心和童心的三毛有一天也會變老。她用她的方式在我們心裡凍齡,今天我們用我們的方式讓她重生。
十三歲小姑因為不適應當時範本式的教育體系,選擇休學。十四歲她開始寫作,當時的作品多半是少女對初戀的期待和懵懂人生的觀察,有著超出同齡孩子的成熟與敏感細緻。童年的拔俗,讓小姑對我和雙胞胎姐姐的教育產生了很多啟發。
我們常常一起去東方出版社書店,在那兒一待就是一個下午,直到抱著一箱箱的書籍往車上搬才願意離開。閱讀是受小姑影響的好習慣,寫作卻是小姑和我都沒想到的一條路,早在那些我和姐姐陪小姑在房間深夜筆耕的夜晚,悄悄種下了因子。
小姑二十四歲去西班牙留學,認識了一生摯愛荷西,也開始了對異國生活的紀錄。《撒哈拉的故事》至今以各種語言在國際上流傳,除了中文版,還有英語、西班牙語、日語、荷蘭語、挪威語、越南語等版本。二十四歲的我來到加拿大溫哥華,踏上異國的土地,沒有小姑當年環境上的艱苦,卻深知小姑當年文化差異上的難處。也許這是命運的安排,又或者是小姑不想離開我們吧!
1979年,小姑短暫回臺北時,我已上小學。初見時覺得很陌生,害羞的我不敢直視她,敏感的孩子偷偷看著這位和其他家人完全不同的小姑。漸漸地小姑成了會開車帶我們到處走的玩伴。常常會遇到很多讀者看到小姑興奮地尖叫,或者叫出我和姐姐的名字呵呵地笑。
看到學校裡的老師對小姑的崇拜,我和姐姐才對這位平常很隨和的玩伴刮目相看——原來她在外人面前是個大人物,原來很多人搶著買她演講會的票,很多人以她為人生標杆學習仿效。那位每天接近中午要我們兩個小孩叫起床的大孩子, 走入我們的童年、青少年,直到如今還是我們身上的標籤和心裡的印記。
我雖然沒有親身參與小姑和荷西姑丈在西班牙的相遇,雪地上的六年之約,結婚後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卻在她書裡不忍心地讀到她的辛苦和堅強。在1970-1980年代的華人世界裡,小姑是讀者的眼,帶讀者看世界。她開了扇窗,無意間做了先鋒,在遠方留下足跡。作為把中西文化交流滲在生活裡的平凡人,她只是實實在在地過日子,卻活出當時千萬讀者想要的樣子。
前陣子聖誕期間我看了一部激動人心的動畫片《尋夢環遊記》,這部動畫片擺脫那種一切都很完美、甜蜜的大主流,拍出了大膽的體裁,著實引起我的注意。電影源自墨西哥的亡靈節故事。講述了一個熱愛音樂的12歲男孩米格不放棄夢想和親情,幫助逝去的親人找回尚在人世的親人的諒解的故事。電影中提到當人世間最後一人都忘記逝世的家人,不再看他的照片,不再談論他,不再想起他,靈魂就會被關在「遺忘區」,再也無法被人記起,也永遠無法投胎。電影有著豐富的文化色彩,滿滿的拉丁風情和神祕感,還帶點小詭異。相信每個人在看這部電影時,都會想起自己逝去的親人,擔心他的現況。我雖然沒有來世今生的概念,卻在電影中看到生與死的樂觀面和現實面。

死亡是一個很多人不敢、不願意觸碰的話題,其實是源於未知和害怕。
逝去,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無奈,沒得選擇只能接受,任你再不願意,也得向上天的決定投降。活著的人不捨,逝去的人又何嘗不是?雙方怎麼放下,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答案,只有用時間慢慢埋葬,眼不見心不想的逃避是大多數人的自救機制。事過境遷,再想起時不會再有當時的熱淚,取而代之的是沉沉地壓在胸口的悶,不用多說,也不想多說。
小姑走的時候是在我高三那年,心情被模擬考試燒壞,那是其他什麼事都不敢想,天真地以為上了大學就一切都會好起來,所以努力忍耐的年紀。1月4日那一天,回到家時家中空無一人,這很不尋常。被課業壓夠了的我和姐姐雖然感到奇怪,也為突如其來的寧靜感到放鬆,誰也不想理誰,各自待在客廳的一角。那是沒有手機的年代,等待是唯一的選擇。我們無意識地開著電視當作背景音樂。正值傍晚的新聞時段,此時電視裡放出小姑的照片,很大一張,她笑得很燦爛,雙手合十,微卷的頭髮自在地垂下,肩上還披著她喜歡的藍綠色絲巾。
我忙著背文言文課文應付明天的考試,並沒有放下語文課本,以為又是一次演講或其他活動的報導,小姑常常出現在新聞主播的口中,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此時,黏在牆上的橘色直立型電話卻驚人地大響,「叮……叮……」我懶懶地起身,慢慢走到牆邊,就在這一秒,新聞主播李四端先生從他口中宣佈了小姑的噩耗,一時間我沒有回過神來,愣住了。
「你們知道小姑的事了吧?」媽媽強忍難過,故作鎮定地說,說到「小姑」兩個字時還是忍不住透露出哭聲。
小時候的我很內斂也比較呆,聽到李主播和媽媽同時宣布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一個第一次經歷死別的高三學生真不知道應該冒出什麼話。
「嗯,是真的嗎?」我停了一下,抱著一絲希望怯怯地問。
「嗯,是的,我們都在榮總。你們自己在家,冰箱有吃的,自己熱一下」媽媽交代完就掛了電話,好像生怕再多說幾句就忍不住眼淚,在孩子面前掉眼淚是母親最不想做的事。
1991年的這一天,大人們在醫院忙著一直沒空,或者也是不知道怎麼開口,所以拖到傍晚才告訴從學校回到家的我和姐姐。當天在學校的我和姐姐渾然不知,還在為了搞不懂的數學和永遠睡不夠的黑眼圈悶悶不樂,後來想想那些都是生死面前的小事。一個最最親愛的家人選擇離開,大人們除了鎮定地處理後事,也只能暫時冷藏心裡的悲傷,為了爺爺奶奶,也為了先一步走的小姑,回到家靜下來時才能釋放,才敢釋放,隔天早上起來又得武裝得成熟淡定,好長的一天。想想做大人真不容易 ,總在生活一次次毫無預警的波折中逼自己成長,誰說碰到這種失去時,大人不會軟弱和無助?忍耐是成長的標配,挫折是人生的顏料,當人離開時,這些都只是傳記裡的劇情,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已經一起埋在親人的心裡。

接下來那幾天,我和姐姐常常處於失去親人和玩伴的空蕩中,在學校時也感到同學和老師的關心。那天導師王姓曆史老師找了班長通知我到辦公室聊聊,我心裡想:不會在這種日子還要訓我那無可救藥的數學成績吧?意外的是善良的老師只是要安慰一個聯考生,並建議如何面對大考在即和人生中第一次失去的課題,還有媒體上的報導和家門口日夜守候的記者。我無法記起她跟我說了什麼,只記得她自己也很難過,數度哽咽,因為小姑來學校演講過幾次,全校師生早已把她當自己人。我只是直挺挺地站著、聽著,不想回話,心裡還是感激的。
上課鈴響時我才跑回教室, 感到許多目光投在我身上。回到座位,桌上放了一堆小紙條,白色的、黃色的、粉紅色的,折成小紙鶴或簡單的對折,那個年紀的女校同學特別溫暖。
那堂英文課我什麼也沒聽進去,下課鈴聲一響,立刻打開紙條,同學、老師們背著我偷偷寫好一字一句安慰和關心的話,再偷偷給我,事後也沒有人再用言語多說什麼。小姑替我選的學校,六年了,今天這個學校的師生們替你安慰了你的兩個侄女,他們也想念著你。
放學回家時,總是膽怯不敢去本該每天報到的爺爺奶奶家。一直堅強保護小姑的爺爺奶奶,此時此刻該如何堅強面對這一切,想到這些,我不知所措。最後還是擠出勇氣跟著爸媽去了爺爺奶奶家 ,只能盡盡陪伴 的孝道,除此之外慚愧地幫不上其他的忙。我從小不是個甜言蜜語、會討喜的孩子,默默在旁花時間陪伴也是當時的我唯一能做的。奶奶拿著手絹,眼淚沒停過,嘴裡說著:「妹妹,你怎麼先走了。」我們不知道怎麼安慰,只知道安慰也是多餘,只能在旁邊杵著。在旁歎氣的爺爺是很瞭解小姑的人,他忍著悲傷和大姑、爸爸、叔叔們商量後事,讓心疼的小女兒走完最後的一程,希望合她的心意,這是這對很不容易的父母能給女兒最後的愛和寬容。
喪禮 上一堆的記者,哭聲混著嘈雜聲。我在心裡問小姑,會不會太吵?她一向不喜歡人多的場合,但也矛盾地希望見到愛她的人記得她。這是一場沒有劇本的戲,出乎意料卻只能接受永遠沒有續集的結局。
這幾年每到一月四日,我常常在三毛讀者的微信群、微博、朋友圈等處看到大家對小姑的懷念。小姑走了快三十年了,還是有很多人沒有忘記她,甚至很多年輕朋友也在時時刻刻說著她的故事,念著她的好,傳揚著她的善。三毛的作品——書、電影、音樂劇、歌曲、演講錄音和訪問,都是她的人生,她的信念。她和荷西姑丈柴米油鹽中的愛,她走過的路,她對親情和家鄉的思念,都是她留給我們的足跡,是她貼心為我們留下的想念她時的憑藉。
在這裡,我的文字也許會讓你再次陷入想念,而我更想轉述的是或許小姑想說而沒機會說的話:「謝謝你們的想念,我去找荷西了。你們要好好生活,偶爾想起我時,請記得微笑和保持自由的靈魂。我的形體已離開,你們的人生要好好繼續。」
爺爺曾在一次訪問中說,小姑只是從人生的火車上提早下車,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終點站。
旅途中相伴一場是緣分,是遇見,是給彼此交集的機會,分開後想起的悸動,是只有你和她才懂的心裡交流。前幾天,西班牙的荷西姑丈的六姐卡門和友人捎來聖誕的祝福,通過網路用中文和西班牙語串聯起對三毛的各種懷念和喜愛。
我終於安心了,小姑不會被遺忘。三毛在用她一貫充滿幽默和創意的方式帶領大家,體會人生的美好與遺憾。故事未完,她的足跡永不消失。
當這本書出版時,我也到了當年小姑離開我們的年紀。是巧合,還是註定?怎麼都好,能夠把這緣分傳承繼續下去,都是欣慰的。
如果你也和我一樣想念她,偶爾在忙碌的夜晚不小心抬頭看到星星也會想起她的名字,她就一直都在,就在那塊我們默默為她耕耘的夢田裡,就在那棵經年累月開枝散葉的橄欖樹下。

本文摘自《我的姑姑三毛:三毛逝世三十周年紀念發行,收錄從未公開的祕密趣事、珍貴照片》,時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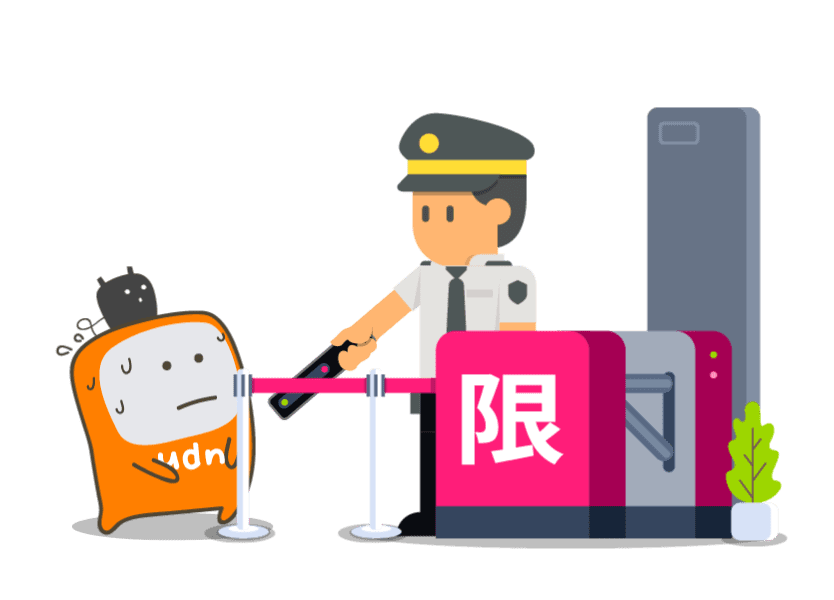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2018%2Fcover.jpg%3F1758878794%3F17588787942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55%2Fcover.jpg%3F1755229041%3F175522904110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863%2Fconver.png%3F1752206769%3F1752206770102)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59%2Fconver.jpg%3F1748316292%3F174831629374)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948%2Fcover.jpg%3F1754878820%3F1754878820386)

/https%3A%2F%2Fprod.jinfm.net%2Fimages%2Fchannels%2F1663%2Fconver.jpg%3F1748333976%3F1748333976770)





















udn討論區